-
您的当前位置: 资讯与投稿 > 玉友投稿文集
- 谈玉雕作品中的人文关怀
- 玉鹤凌风 / 1月25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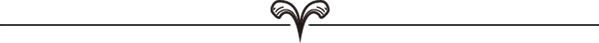
做了六年记者,养成了喜欢品头论足的坏毛病,坏到喜欢吹毛求疵。
比如,听一个正在为海南一个叫乐东的县做战略规划调研的人说,“城市需要经营”,我就觉得,“经营城市”显得老套,早在大连大搞城市形象的时候,“经营城市”就已经畅销中国,然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再说经营城市,显得落伍。我们在追求外表的整洁美观的同时,也产生了公平、自由、个人理想等深层次的需求,我们不仅要环境漂亮,还要节能环保,我们不仅要GDP,还要绿水蓝天,我们不仅过的富于充足,还要实现人生价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只是强调“投入产出”的经营城市理念,在这个时代,稍显粗放了些。
我们不拒绝高老大厦,富丽堂皇,但是也不能忘记,这个社会还存在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文明的底线,也考验着精英阶层的人文观念、道德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财富)越应该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生活如此,艺术的创作亦如此。这应该是艺术的人文关怀吧。
笔者曾经听一位国内非常有名的玉雕大师讲,“在美术学院里,搞绘画、书法、雕塑的人总是比搞工艺美术的人要高一个等级。”这大概是从艺术作品的批判性或者人文关怀上来说的。
当搞绘画的文艺青年用贫穷的日子批判着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的时候,工艺美术工业者正在按照价值规律创造财富,艺术的价值往往由物品的商品属性表现出来,比如这件作品多少钱?材料有多稀有?工艺水平往往最后考量,至于材质与工艺综合表现出来的艺术水平,审美体验,总是在实现商品价值之后才会慢慢被人注意。这大概就是某位大师说说的“低人一等”的原因吧。
玉雕属于工艺美术行业,也是一门吉祥艺术,玉必吉祥,玉雕艺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原本显得格格不入,少了对事物的批判,便少了思想的深度,只能在赞美与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方面穷尽可能。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的玉雕作品多见“升官发财”、“指日高升”、“年年有余”、“平安无事”、“事事如意”、“祝福”、“和合二仙”等等,这是朋友之间,家人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可以看做是普通人之间的问候,就像“你吃了吗?”这么简单。这样的关怀,谈不上道义,更无所谓高尚,但是一句“祝你平安”还是能够感动人的。所以诸如上述题材,亦是一种人文关怀。
玉雕之中,还有文字题材的、宗教题材、历史人物题材、山水题材、动物体彩,不一而足。这样的题材多不是直抒胸臆,有些甚至让人看不懂,产生神秘感。例如上海海派玉雕的崔磊,他的作品《圣功》以文字、图案搭建起来的视觉效果,肃穆、庄重,很多人一下子可能看不懂“天地玄黄”什么意思,却能从作品的整体效果中感受“文化的起源、天地的造化”这样的审美体验,进而激起观赏者对本民族文字、文化起源的神往。作品自然而然的满足了人们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好奇心,增加了对自我文化的肯定和认同。
山水题材脱胎于古代文人山水画,其中以山籽、玉牌最为常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无常形,多变化,而正是在这千变万化中,孕育了生命,产生了智慧;山,巍峨耸立,坚毅挺拔,正如君子“仁义礼智信”的品格,故仁者乐山;因此,以追求人生最高境界的中国传统文人或愤懑于“世人皆醉我独醒”、或开悟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踌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隐居于山林,“弹琴复长啸”,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同,性格迥异、志向不同,然而他们却大多钟情于山水,亦唯有山水才能明志明心。究其原因,还是孔子所倡导的,人生的最高境界“非智者,便仁者”。因此,文人以山水表露心迹,以山水为题材的山籽、玉牌则体现了人们对人生最高境界的追求。因此,山水玉雕的人文关怀,毋宁说是对人生的寄语,其具体又抽象,是最高境界又非仙非道,存在于你我之间。
因此,玉雕作品中充满着人文关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如此。笔者发现,玉雕作品越做越大,题材却越来越单纯,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艺术价值、人文关怀却接近于无。一件作品横空出世,留给人们的往往是,“它值多少钱?”“他做了多长时间?”“它是不是最大的”这样的追问。此时,艺术让位于价值规律,关怀让位于关注,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大而无当”。


